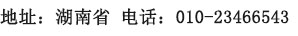尽管随着科技进步和医学发展,人类在疾病防控以及卫生保健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诸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以及各类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疾病,仍然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在古代中国,瘟疫是对各类传染性疾病或人群大规模罹患疾病现象的泛称。在与各类疾疫长达数千年的搏斗中,中国人民凝结了诸多防疫祛疾的经验和智慧结晶,诸如《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当下新型冠状病*“SARS-CoV-2”引发的肺炎(COVID-19)疫情严峻,笔者特撰此文,意在观古通今,知往引远。
殷商时期的疫病认知与防控殷商时期的疫病认知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疾患、医疗万面的记录。多年来,经学界不断探索,我们对殷商时期的疾病及医疗保健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①值得注意的是,据甲骨卜辞判断,殷商时期人们对于突发性疠疫瘟疾已有一定认知,并积累了许多抵御疾病传染、防控疫情蔓延的应对办法和社会俗尚。群体性突发疾疫在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如:贞疾人,隹父甲害。贞有疾人,不隹父甲害。(《甲骨文合集》z)疾人,隹父乙害。不隹父乙害。(《合集》反)这是一期武丁时的两版卜辞,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有关疾疫文字记录。此卜辞中的“疾人”与专指某种疾病或患者的“王其疾肩”、“埽某疾齿”、“子某疾目”等辞例不同。“疾人”之“人”,与“贞我其丧众人”(《合集》50)、“告其丧人”(《合集》)、“于滴丧人”(《合集》)、“邑人”(《合集》)、“尔以西人会我”(山博甲8..1)、“立人三百”(《合集》)、“登人五千”(《合集》)之“人”相同,是指众多的人,大略涵盖殷商王朝治下社会各阶层人群。“疾人”泛指人群间发生的大规模突发性、流行性疾疫,相当于《说文》所云:“疫,民皆疾也。”《礼记·月令》:“民殃于疫。”《字林》:“疫,病流行也。”《释各·释天》:“疫,役也,言有*行疫也。”当时人们视此类疫病为已故先王父甲(阳甲)、父乙(小乙)等人*作祟降灾以示警 ,与《逸周书·祭公解》“天降疾病”的疾疫心理观存在代差。③甲骨文又有云:乍n父乙女,妣壬豚,兄乙豚,化口。午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合集》)口子1、,钾o即…一女……(《合集》)上引《合集》,为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灰坑发掘出土的大牛肩胛骨卜辞,原拓见《小屯南地甲骨》①附册F3.1。“乍疫一午口众”两辞同卜。九d:‰,亦写作岭(《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⑤),从广从殳,实即疫字,指疠疾瘟疫。“乍”有作成、产生、突发、发生之义,《东大》①:“贞其有乍害”,《合集》:“贞王有乍祸”,《合集:“贞子妾不乍莫(艰)”,可见其义。“乍疫”谓突发流行性疠疫。卸,御也,义为御息病灾。“御众”、“御疫”,言疠疫乍起,为众人御祭以弭息疫情蔓延。御祭中,先祖父辈祭牲用大牛及豢(豪豕),先妣和兄辈用小豚与卢豕(即黑毛猪。《释名》:“土黑日卢。”),等而祀之。应注意的是,《合集这版卜骨,祭牲字的头部都被刮削掉了,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巫术御疫诅咒的心理观念。“御众”,御疫对象是众人,说明疠疫染患是群体性的,这是疠疫的特征之一,与上引《说文》“疫,民皆疾也”相符。《*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②疠疫染患的群体性就在于民众“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卜辞的“御众”,即是针对群体性染患瘟疫的众人施以御除病殃之祭。一期甲骨文还有云:丙辰1、,贞。丙辰1、,疾。(《合集》)辛丑,贞疾。辛亥,贞邑自。(《合集》)两组卜辞中的“疾”,訾指疠疾瘟疫而言。自,步若列也,读如烈,有暴烈、猛烈、剧烈之义。辛丑日问疾疫,十日后(辛亥)卜邑烈,涉及疠疫发生所及的邑聚地点,以及担忧疫情在邑聚中传染蔓延的猛烈态势。我们在整理山东博物馆馆藏甲骨文时,又发现下面一组武丁时有关“疾年”行事的卜辞:贞【燎]于东于西。贞正。贞燎五牛,正。贞正。贞于高燎。贞有疾年其歹盖。(山博8.5.3+8.33.17,即《合集》+)“疾年”,④年谓年岁季节,意思类同《周礼·天官·疾医》:“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变救》:“寒暑失序,而民疾疫。”①《*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冬伤于寒,春必温(瘟)病。”②殷商时期不仅认知到疠疫瘟疾有群体性特征,还意识到有季节性特征,年岁中季节转换、温湿度或气候反常以及其他自然或人为因素,都可能引发瘟疫大规模传染蔓延。《墨子·兼爱下》:“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东汉王充《论衡·命义》:“温(瘟)气疠疫,千户灭门。”③卜辞“疾年其媪”,媪意为媪殁欲死,即是年内疠疫流行而致人死亡。“疾年其媪”来自对疫病起因后果的忧思与其不可知性的恐惧,也体现着面对不断扩大的疫情,统治者的心理焦躁和对社会情绪浮动的担心。“于东于西”可读如“于东与西”,加上“于高”,并列三个燎祭地点。“正”有正成、平息、以正受祜之义。《诗·大雅·文王有声》:“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上揭六辞反复卜问在东、西及高等几个地点燎祭防控“疾年”之灾,能否祛除瘟疫,求得平安护佑。甲骨文又有云:己巳l-,兄,贞其燎于盟室,玄小字。(《英国所藏甲骨集》④)己巳1、,王,于围辟朗燎。己巳l-,王,燎于东。(《合集》)这是卜问举行熏燎窒屋、门道与东边野外场所的祭祀行事。熏燎防疫可追溯到更早时期。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年前人们已掌握薰燎樟科植物叶片来杀灭病虫,净化生活场所。⑨《周礼·秋官》有云:庶氏掌除*蛊,以攻说袷之,嘉草攻之。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以嘉草、莽草熏燎除蛊驱虫防控疾疫,流传于后世。如北宋刘延世编《孙公谈圃》云:“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⑥此后还衍生出熏蒸消*祛除瘟疫的民俗,甚至见于行*征战的紧急场合。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8《服器部》云:“天行瘟疫,取初病患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此是后话,不赘述。驱疫祛病的方式方法面对瘟疫袭来,商代人采取的应对方法,既有囿于认知水平和宗教观念的非科学应对手段,也有基于理性思考的防控措施。甲骨文中记载有以巫术殴驱疫*行事:庚辰,贞口降*,允隹帝令。庚辰,贞其卑*。(《合集》)“降*”与“每*”同贞,“降*”是视瘟疫为上帝命疫*降临所致。“譬*”的每字,如手执某种十字交器具,盖指装扮*巫殴驱疫*的法器。《论衡·订*篇》:“巫者为*巫。”①《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殴疫”,郑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殴疫疠之*,如今魃头也。”方相氏戴*面具执戈扬盾,率领百人举行殴*祛疫的大型巫术活动,殷人手执十字交法器殴驱疫*与之类似。出于防御瘟疫蔓延,甲骨文中还有“宁疾”以求消除瘟疫的祭祀行事:贞今日其宁疾【于四方],三羌九犬。(《屯南》)壬辰1、,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叉九犬。(《屯南》)甲申贞,其宁疾于四方。(《屯南》+,《醉古》②)即向四方诸神祭祀,以求宁息瘟疾之灾,祭品用三个人牲羌奴和九条狗。《史记·封禅书》云:“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③面对瘟疫,殷商统治者也采取了比较理性的作为——隔离防控措施,同时又意识刭要禁止谣传。比如一期甲骨文有云:辛丑1、,亡疾。辛丑1、,亡口。辛丑1、,贞疾蚀,亡亦疾。(《合集》)壬寅1、,亡口。亡入,疾。(《合集》)口戌1、,口亡入,口疾。(《合集》)彳虫同如蚩,害也。“疾害,亡亦疾”,“亡亦疾”是“亡疾、亦疾”的急语,盖面临突发的疾疫之害,再正反两问“亡疾、亦疾”,反映了恐惧心理。①“亡口”与“亡疾”、“疾害,亡亦疾”、“亡人,疾”同卜,“亡口”意思是毋传播谣言。《尚书·盘庚》:“其发有逸口”,“罔有逸言,民由丕变”,“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谣言惑众,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造成民情不安,社会动荡,故必须“度乃口”,杜绝流言蜚语。①“亡人,疾”则谓不得轻易进入疾疫场所,否则会招致扩大传染之祸。犹如《周易·复·亨》云:“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无妄·元亨》:“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可与出入无疾的朋友交往,如果是疾病患者或眼疾患者,则不应过近往来接触,以免传染遭殃。《周礼·天官·疾病》云:“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师。”《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②甲骨文所言“亡人,疾”,与“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舍空邸第”的隔离措施类似。药物医疗与防疫,商代之前已然。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1件距今约年的小陶釜,外底有烟炱痕,釜内盛有一捆20余根植物茎枝,经检测为“单方”“中药罐”遗存。④甲骨文中记殷商武丁时设有“小疾臣”(《合集正反)的专职医官。《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之言:“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清华简《傅说之命》亦云:“若药,如不瞑眩,越(厥)疾罔瘳。”④意思是如果服药后感觉不到头晕目眩的药物反应,病未必能治愈,这是对某种药性药力的感受体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一座墓葬.随葬品中有卜骨3块及1个长方形漆匣,内装“石砭镰”针灸医疗用具,墓主为45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生前应是位巫医。⑨《逸周书·大聚解》记武王灭商后效仿“殷*”,“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⑨《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⑦《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鼢、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抱朴子外篇·仁明》:“疫疠之时,医巫为贵,异口同辞,唯论药石。”cs]巫因*神崇拜而产生,巫医不分,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立巫医,具百药”,反映人们在直面疠疫中伴随着无数次痛苦教训而日积月累取得的医疗经验。①《合集》:“多口,亡祸。多言,亡祸。”《英藏》:“亡乍口。”均是讲不要多口多言,摇唇鼓舌,造谣生非,不然会引发祸害的。《尚书书序·商书》及《古文尚书·说命中》有云:“惟口起羞。”《礼记·缁衣》引《兑(说)命》作“惟口起羞”,郑注:“羞,犹辱也。惟口起辱,当慎言语也。”参见拙著:《商代史》卷7《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绪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窒熏鼠。”《诗·豳风·东山》:“洒扫穹窒。”毛传:“穹,穷;窒,塞也。”笺:“穿窒鼠穴。”严一萍谓“寇寝”之寇,像以殳殴驱虫虺于室外,又谓“今俗端午节犹以雄*酒浸喷洒居室四壁,以辟恶除*虫疾疫,其即水寝之遗意欤”。①《周礼·秋官》:“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用蜃炭涂抹室屋的墙壁,能除鼠虫*菌,与甲骨文言预防疾疫的“水寝”,作用类似。三、个人保健与疫病防治就个人而言,卫生保健是抵御疾疫病*侵害的一道重要防线。商代考古遗址每每出土盥洗用器。殷墟侯家庄号大墓东墓道曾发现一套青铜盥洗用具,一件承水铜盘倒扣在一件“寝小室”盂上,旁边有沃水勺和贯耳汲水壶一个,还有5个直径10厘米大小、搓擦身垢用的陶颊。②甲骨卜辞有云:贞于塾用。(《合集正)贞小子有鱼。(《合集》正)罗振玉谓笾字“注水于盘,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⑧《说文》:“浴,洒身也。”《论衡·讥月》:“浴去身垢。”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甲骨文云:口酉,喜。弱鸯。二辞正反对贞,与沐浴洁身相关。“鸯”像一女湿身盆中“浴去身垢”,与“垫”、“鱼”同字异构,从女、从入通作。c年安阳孝民屯的商代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一件铸范,平面圆形,直径达厘米,折沿,沿宽约7厘米,是一特大型青铜盆形范,可铸造用作个人沐浴洁身的硕大洗澡盆。⑤强健的体魄,可以有效抵抗疫病侵袭。《吕氏春秋·古乐》:“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追述上古洪水泛滥,渲泄不畅,人们情绪郁结,筋骨萎缩,手足肿胀,体质虚弱,疠疫多发,于是通过某些伸展运动,调节情绪,增强体魄,减少疫病侵染。甲骨文亦有云:贞中子肱疾,呼田于凡。(《合集》)即中子的胳膊有疾,让他去凡地参与口猎活动。可见当时已意识到野外口猎活动是一种积极的运动锻炼,能舒筋活络,调理血气,有利于疾患痊愈。 ,不妨讲述一位在殷墟《花东》甲骨文中的“子”(武丁时的王室成员)在健康状况不佳时,如何通过坚持运动锻炼来抵御疠疫的事例。《花东》记“子心不吉”,即子感到心区不安吉。《花东》记子“今又心魃”,形容子心绞痛似棍棒敲击一般。《花东》记“子疾首亡延”,即头痛不已。《花东》又记下了“子耳鸣”。据《*帝内经》,经气厥逆或精血不足会引起耳鸣。《花东》记“子目既疾”,《花东》59谓子“目丧火”。据《*帝内经》,眼疾有目痛、泣出(流泪症)、目赤、眦疡、眼睑水肿、视歧、目翳(白内障)、目盲等。“目丧火”,似指目赤之类红眼病。《花东》谓“子口疾”,可能是患咳嗽、口腔炎症、嚼咽困难或构音障碍之类的疾患。《花东》记“子腹疾”。由此可见,子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可谓周身是病。但是,下面一系卜辞则反映子并未沉沦,而是通过积极的身体锻炼,以增强体质、减轻疾息:己1、,子其疫,弱往学。庚1、,子心疾亡延。壬1、,子舞不又,亡言,丁永。(《花东》)甲寅1、,丁永,于子学商。用。丙辰1、,延奏商。用。(《花东》)丁卯1、,子其入学,若永。用。(《花东》)丁丑1、,在主京,子其玄舞戌,若。(《花东》)“子其疫”,即子染上了某种疠疫;“子心疾,亡延”,谓子患心脏病缠绵不已;“亡言”,古文字言、音可通,谓病不能出声,《*帝内经灵枢·忧恚无言第六十九》:“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①“往学”、“入学”犹言就学。“子舞不又”,不又为族名,相当于文献中的舞散乐。《周礼·春官·旄人》:“掌教舞散乐”,郑氏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皆有声歌及舞。”“学商”、“奏商”,《花东》又提到“子用我瑟……舞商”。“商”是一种类似于融器乐、歌辞、舞蹈三者一体的祭祖舞,属于所谓“文舞”。“舞戊”,戊为斧钺类兵礼器,执钺而舞,当是武舞的一种。②《礼记·乐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郑氏注:“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执。”这一系卜辞,具体而微地记下了子尽管染患疠疫,又有心疾等多种基础性疾病,厌于说话,却仍坚持就学,不仅练习不又舞、商舞等文舞,还学习力量型的执钺武舞。可见子是一位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坚持锻炼身体以抵抗疠疫的人。综上所述,我国最早关于瘟疫的记载可追溯至殷商时期。甲骨文的“疾人”、“乍疫”、“疾年其媪”、“疾一邑烈”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疫病发生、传播以及危害性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殷商统治者在面对疫情肆虐时,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烈的心理焦躁和对社会动荡的担心;另一方面也采取多种手段来防控和治疗疫病。受限于殷商时期信仰观念和医学知识,当时采用的防治策略,既有“御疫”殴驱疫*、“宁疾”以求“御众”消除疠疫等巫术祭祀,也有隔离防疫、禁止谣传、熏燎消*、药物医防、饮食保健、洒扫居室、清洁环境卫生等理性、科学的防控办法。而那位久病体弱又罹患疫病的“子”的事例,则展现了积极乐观的精神品质和运动锻炼强身健体,对于抵抗疫病侵袭、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殷商时期,在疠疫瘟疾猖獗之际,人们井非束手无策,而是通过国家行*、社会群防、运动保健等方式,积极抵御疫病侵害,形成了许多预防疠疫传播的社会风尚和习俗,其内容涉及医药学、环境学、营养学、卫生保健学、心理学、体育学等。散积久演的疠疫防控行为,标志着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