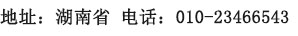楷书中的“笔势”
楷书晚出,有人指出甚至可能在草、行之后。然而楷书在书法步入鼎盛时代后被认为是书法艺术基础的书体,也是人们刻意求精、名家辈出的主要书体之一。
自楷书出现,迄今己近两千年,书艺在中国长盛不衰,代有才人,却再也未见字形有较大变革的新书体问世。楷书在书法艺术领域具有特殊地位的事实,是值得深思的。与其他各体比较,楷书的字形结构和笔画安排更为统一。书写的规范更为严格。故地称为“楷”、称为“正”(也作“真”)。作书者欲以楷书表现自己的感情、志趣和个性,需要极深的功力和造诣。 的书家能在楷书的运笔、间架结构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那也是在十分严谨的体式规范基础上的创造。
书法艺术的兴盛,尤其是楷书的流行,使人们更注意探讨书法的范,书法理论于是出现分解汉字的趋势。不少论者幵始从基本的一笔一画着手,去探索书艺美产生的机制。这就是“书势”论为“笔势”论取代的根本原因。
在“笔势”论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永字八法”。八法者,‘永’字八画是也。”所谓“永字八法”,其实就是分解“永”字八种笔画的书写要领,使学书者掌握毛笔写字的基本笔法。“八法”为“隶”体的书写规范不过汉代亦称楷书为“隶”,从“趨”、“啄”等笔画的名称看,已是楷书笔势。“八法”即:
“点”一点为侧。
“横”二横为勒。
“竖”三竖为努。
“钩”四挑为趨。
“提”五左上为策。
“撇”六左下为掠。
“短撇”七右上为啄。
“捺”八右下为磔。
永字八法将每一种笔画的都成为是一种“势”,“八法”就是“八势”,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解读。将每一个笔画名称强调突出是为了将书写笔画的运笔方式、使劲方式以及字形特点用形象化的解读来突出其特色。不仅在笔画称呼上直言为某势,可以说完全是从“势”的角度来讨论基本笔画规范的。这就为我们理解“势”的特点提供了方便。
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成是由动到静的过程。字形地服从表现“势”的需要,许多书法家自觉地以造势来把握自己的艺术创造。从这个角度说, 呈现于纸面上的“形”,是“势”所造成的。
“势”和“形”的联系密不可分,在“形”中才能够将“势”表达出来。但是,只有“形”并不能解读出“势”。如果说两者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那么瞎写乱画中也会存“势”了。所以说在书法创作之中严谨的规范必不可少,只有遵循了规范才能够创作出有质量的书法作品。“永字八法”就是楷书笔画的规范,作品一旦完成,书法家创造的美的字形就己经凝固。
欣赏者从这凝固的形所具有的“势”中可以体察到书写者运笔的过程和势态,以至他的功力、情性和艺术追求,也完全可能超过书写者当初赋予作品的意趣触发更广泛的联想,这种看来是静止地形,必须显示出运动的趋势,具有动态的美感和流转的活力,必须在合乎笔画以及间架结构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出超越“形”的意蕴。简言之,艺术活动(尤其是欣赏)中更重要的是由静生动,以形生势的一面,有势之形必然是富有包孕的形。
笔势与笔力、速度的关系
追求笔势的目的之一是显示笔力。所谓笔力并非简单地加大、加重运笔力量就能获得的。书法家中以笔力遒劲知名者,不少是文弱的一介书生,赳赳武夫精于此道者却为数不多。笔力实际上是凝固于纸面(或其他材料)的笔画造型所显示得力的内蕴。书写者恰恰要在运笔的一定阶段及时地“轻揭”、“轻挫”施以“轻锋”,才符合笔势生力的要求。相反,在这种场合用力过于滞重,则“势肥”,甚至成为“多肉微骨”的“墨猪”。《笔阵图》讥斥“墨猪”、褒举“多骨微肉”的“筋书”,是因为自然物态中“肥”是弛缓无力的表征,而“筋”、“骨”则有劲健之力的内涵。故云:“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运笔的速度与“笔势”的关系密切,《石室神授笔势》云:“书有二法:一曰疾,一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能以较高的速度疾书,常常是作书者熟练掌握书写技巧和具有奔放不拘个性率意挥毫的表现。“疾”能生势是容易得到人们首肯的。然而“笔势”论对“涩”、“徐”、“迟”的重视却耐人寻味。《八法详说》论“侧势”云“疾则失中,过又成俗”,说明并非一味求速就能得“势论“努势”云“努势之法,竖笔徐行”;论“策势”谓“始筑笔而仰策,徐转笔而成形”;论“磔势”则“势欲险而涩”,还有强调须“疾”与“涩”“迟”相结合的,其论“掠势”云:“拂掠,须迅其锋,左出而欲利”,“以轻驻其锋,右揭其腕,加以迅势出,旋于左。法在涩而劲.意欲畅而转,迟留则伤于缓滞”。
只有“啄势”“须疾为胜”,“啄笔速进,劲若铁石,则势成矣。”这里用到一些意义相近的词,需要把握好分寸,“涩”虽曾与“疾”对举,但它不能与“徐”、“迟”等同,除了行笔速度较慢以外,还有加大增大笔纸摩擦以追求一种特殊用笔效果的意义。论中“涩”、“徐”是受到肯定的,而“缓”则毫无可取;大抵“涩”、“徐”之法有助于笔力吧。看来,“笔势”论绝不是盲目地以“疾”“迅”为好的。“八法”更多地肯定了“涩”、“徐”的必要,固然由于它论的是规范化程度 的楷书笔势,也因为此时人们在运笔技巧上的探索己经精细入微,不再满足于简单地以速度快慢论高低了。
运笔应有疾有徐,相反相成;须服从取势的需要,该疾则疾,该徐则徐。它们常常互相转换,互为准备或过渡阶段,徐有时是“存势”所必须。疾徐相间不仅显示出力的张弛和蓄蕴迸发过程,也是创造书法艺术节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后宋代姜夔《续书谱·迟速》云:“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清人宋曹《书法约言》说:“盖形圆则润,势疾则涩,不宜太紧而取劲,不宜太险而取峻。迟则生妍,而姿态毋媚;速则生骨,而筋络勿牵。能速而速,故以取神。应迟不迟,反觉失势。”
由此可见,笔势与笔力、速度均有一定关系。
笔势的运动和趋向
书法艺术并不再现或者表现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象,笔墨线条能唤起人们对某些物态(包括有力美意蕴的劲健、挺拔、飞动之类物态)的联想,但毕竟不是图画。书法艺术力求表现一种特有的力美,要求笔势具有生机勃发的律动的活力,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艺术家对万物生命运动的理解相契合。
笔势,从起笔、行笔、收笔,就一直伴随着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笔势的体现。每一次运动都伴随着书家对笔势审美趋向的选择。而审美的趋向又大致取决于书家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作书者能否有表现美的自觉意识和审美经验,他应该对笔势美的所在和构成了然于心,就“意在笔先”而言,这是“意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二,作书者能否得心应手地驾驭书法艺术的媒介(笔、墨、纸),以运动变化(包括轻重疾徐)的线条创造理想的笔势。
书法不直接描摹和表现客观世界的具体物象,却强调创造灵动的“势”,表明传统艺术领域认可生命运动的普泛性。看来书法家对“势”的追求与我们民族的人与宇宙同构的意识有某种默契;而表现出艺术形象的生命运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现的方式,无论是否能在客观的世界现象中找到它的同类)乃是书法艺术创造的灵*。
为什么说“体势”是书法艺术形式的表现
结字的“取势”之道
《九势》“阴阳向背”、“藏头护尾”、“上覆下承”之说所涉及而未展开的间架结构问题,是构结“字势”的关键所在。其后,张怀瓘在其书论中,对结字之法做了详细的归纳。
张怀瓘论《用笔十法》云:“一、偃仰向背:两字并为一字,须求点画上下偃仰离合之势。二、阴阳相映:阴为内,阳为外;敛心为明,展笔为阳。必须相应,左右亦然。三、鳞羽参差:点画编次,无使齐平,如鳞羽参差之状。四、峰峦起伏:起笔蹙衂,如峰峦之状,杀笔亦须存结。五、真草偏枯:两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谓之偏枯。须求映带,字势雄媚。六、斜正失则:落笔结字,吩咐点画之法,须依位次。七、迟涩飞动:勒锋侧笔,字须飞动,无凝滞之势,是为得法。八、射空玲珑,谓烟感识字,草行用笔,不依前后。九、尺寸规度:不可长有余而短不足,须引笔至尽处,则有凝重之态。十、随字转变:如《兰亭》年”一笔作悬针,其下“嵗”字则变垂露;又其间一十八个“之”字,个别其体。
这“十法”之论可谓要言不繁。很显然,其“结字”的宗旨就是形成理想的“字势”,我们可以对“十法”提及而它论未详的几个问题略加释评。汉字的合体字比独体字多得多。张怀瓘指出“两字”(其后“三字”亦同)并为一字,须求点画上下偃仰离合之势,即要求新的组合须是有机的统一体,以两字间的点画照应和“偃仰向背”组成一个有生动势态的新结构,其后“真草偏枯”一法也反对合体字真草杂凑破坏整体字势的和谐统一,要求以划一的书体相互“映带”,创造“雄媚”的“字势”。
“阴阳相映”一法说得明白,书法的阴阳之道就是“字势”的内与外,“敛心”与“展笔”,左与右相反相成。“敛”与“展”也即收与放、合与开。“阴阳相映”似乎有两层意义,一是“势”的内蕴(“心”)和外在的形(“笔”)两相映衬;一是“字势(包括内蕴和外在形态在内)收放、开合、左右的两相映衬。书法论标举相反相成的阴阳之道,虽然阴阳五行说原属自然哲学,可是在书法论中人们己经运用阴阳的对立统一和五行的相克相生辩证地阐释了艺术的造型问题。“鳞羽参差”一法以“无使齐平”为要,力求以重叠交错的丰富层次克服造型的单调平板。“峰峦起伏”之法中“杀笔亦须存结”一语颇为精辟。“杀笔”,即收煞之笔,“存结”指留存余势。张怀瓘要求作书者笔止而势不尽,创造出包蕴无穷发人遐想的意象。
“射空玲珑”一法尤其耐人寻味。所谓“射”即是“象”,是取法某物的意思,“玲珑”为精妙的造型。“射空”指无所依傍,凭空臆想得来的笔法,所以后文以“行草用笔,不依前后”来解释。因为行、草两种书体的随意性大,为造诣高深的书家提供了“不依前后”经验规范、以其创格达到精妙的条件。而“烟感识字”又是“射空玲珑”的基础,所谓“烟感识字”大抵是要求书家根据自己的朦胧感受来把握字的意象,看来这是一种强调表现心灵模糊感受,从“有法”升华到“无法”的高层次艺术创造。
体势是书法艺术形式的表现
张怀瓘在品评书艺的时候是很重视“势”的,他指出王羲之“研精体势,无所不工”,又说“卫恒兼精体势”。可见,“体势”事关艺术表现的成败,故书法家必得“精研”之。“体”与“势”有时候虽然连成一个词,它们其实还是保持着各自意蕴的。
“体”对于书法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具有体制和基本倾向方面的指导意义,在书艺创作过程,它体现于“布置”和“预想字形”中,是作书者对整个创作的安排和构想近乎艺术造型的蓝图。在欣赏者来说,它是从总体艺术形象中体察出来风格和形式规范。“体”的指导意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它可能来自各种书体的传统规范,也可以来自书法家固有风格的规定性,抑或出于临池作书时有关布局和字形的某种特殊构想。
“势”在书法中可以看作是笔墨运行过程展示出来的艺术效果。正如虞世南指出的那样,书法之势与用兵的阵势一样无常,与水火的形态一样无定。仔细体会张怀瓘等人所论的灵活无定、富于变化的“势”,其产生过程也有不同情况:有在预想中安排布置的,即出于“意在笔先”的;也有“心手随变”出来的。预想之“势”与“体”的关系最为直接。不过,就一个成熟的书法家而言,“心手随变”虽然是灵活无定的,却总与他的工力、风格和艺术追求等与“体”相关的因素有潜在的联系。
张怀瓘的“体势”论推崇灵感,推崇创造性,推崇“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所以他强调“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盛赞“得之自然,意不在于笔墨”,肯定“亦别成一体”的成就。
《玉堂禁经》曾指出:“夫书之为体,不可专执;用笔之势,不可一概。虽心法古,而制在当时,迟速之态,资于合宜。”在书法艺术创造中,遵循“体”的规范不可刻板,运笔取“势”不宜雷同。前人树立的典范诚然应该有所效法,但是对书艺最重要的却是因时制宜。此处“制在当时”可以理解为“体势”的创造合乎书法家所处时代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作书的“当时”对一幅作品“体势”的抉择。可见“体势”与风格和书法家的人格是完全吻合的。
▍扩展阅读:
同样是“衰年变法”,为何*宾虹成功,陆俨少失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