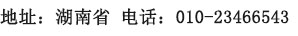王资鑫
清代后期,另一位书论指南的分墨者,叫刘熙载。他是扬州府兴化人。十九世纪的苏北里下河居然出了位被称为“东方黑格尔”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应当是江淮水乡的骄傲。
刘熙载出生于一个“世以耕读传家”的寒儒家庭,那是嘉庆十八年,父亲虽为隐士,却有声望。刘熙载的童年悲剧是,十岁丧父,数年复丧母,所以少孤贫,但力学笃行。道光十九年,二十六岁的他乡试中举;六年后赴京会试,以文书均优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三年,他40岁时值上书房,咸丰帝见其体气充溢,问其所养,刘熙载答以“闭门读书”,遂得御赐手书“性静情逸”四字。咸丰六年,朝廷考察群吏,刘熙载名列前茅,本可仕途再进一步,可刘熙载偏在官场找不到自己,不乐为吏,不忘沟壑,遂下山东禹城,开办私塾为生,教书两年,“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名满当时,继而被延请到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
十年浪迹浑闲事,知负淮南几树春,一段漫游生涯后,同治三年秋,他被命为广东学*,慎独主敬,四箴勉学,三年督学,任期未满即请假归里,从此脱离官场。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六年,刘熙载将他生命的 十四年,全部奉献给了上海龙门书院,身兼学者与导师,以正学教弟子,格物致知;与诸生主讲习,终日不倦。刘熙载终于寻到了他 的生存状态,讲堂与书桌成了他安放灵*的 居所。光绪六年夏,刘熙载因寒疾不愈,回归故里,来年卒于古桐书屋,享年69岁。诸生千里赴吊,《国史·儒林传》褒其“品学纯粹,以身为教”。
今天,我们从后世观察者的位置看刘熙载,这位翰林院编修的毕身大成,倒不再*绩,而是一在治学,二在教学。他的学术贡献遍达经学、子学、史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无不涉猎,靡不通晓,博学躬行,明心见性。诸如教学随笔《持志塾言》,音韵学专著《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伦理学专著《持志熟言》,诗文词曲专辑《昨非集》,汇刻本《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而刘氏书谱中, 分量的要数《艺概》。刘熙载凭“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之法,以《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论述古典诗、词、曲、赋、散文、书法的流变、创作、鉴赏、特征、技巧,成了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与刘勰《文心雕龙》比肩的通论文作。而其中研究书法理论的精华,汇于《书概》,多条系列化的精湛论叙,内容涵及“论”与“史”两部分:
“论”首先提出“人品论”,刘熙载认为“书当造乎自然”,作为第二自然的艺术美,渗透着人为的因素,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成果。而“书”是什么?“心学也”,写字写什么?“写志也”。书,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这里,刘熙载强调的是,笔性墨情,以人性为本;理情者,书之首务也。这一书品与人品统一的命题,规范了书法与书家关系,指明了书家首重内在修养的人格道路。此外,《书概》还阐述了学书途径的“方法论”,书法用笔点画、结字章法的“技巧论”,关于书法骨力、品第、风格的“书品论”,关于书法创作动机,艺术构思,表情达意的“创造论”,体例新颖,观点精辟。
“史”先叙书法演变史,论及各种书体的产生、发展、概念、特点,指出篆书要如龙腾凤翥,隶书需取势险节短,特别对草书个性的阐发更是鞭辟入里,诸如草书注意多于法,结体贵偏而得中,重笔力,重筋节,用渴笔,先遗形,居动以治静,画省而意存,都属于独创性的书体标准状摹。“史”的第二部分是书艺发展史,论及历代书家作品,不囿门户派别,不乏真知灼见。
读解《书概》,给我们最醒豁的感觉是,其概括性和哲理性已属难能,而可贵更在其辩证性。明隽整饬的论证,处处闪烁着对立统一观的朴素异彩;行笔之速与迟,提与按,涩与疾;笔意之摄与振,虚与实,全与半;字体之曲与直,圆与方,简与详;用笔之中锋与侧缝,藏锋与露锋;结体之疏与密,动与静;字形之内抱与外抱,放纵与内敛;章法之阴与阳,意与象,整齐与参差,平正与欹侧。形神互映,意法相成,《书概》达到了书法美学体系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堪与唐孙过庭《书谱》双峰并峙。
刘熙载自少至老,表里浑然,未尝作一妄语。《清史稿》《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传其一生,唯有书生本色,儒者气象——为此,后人才对刘熙载和所有书法理论耕耘者饱含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