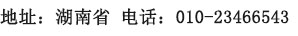发源于昆仑山的塔里木河,水流悠悠流淌不息,默默蓄积的耐力和韧性,渐渐穿透了沙海与戈壁之间的地面阻隔,接触与碰撞,沟通与达成默契,终于被水的力量牢牢地焊接在大地的板块上,而将生命的根须深入到地下,一条河流的历史就这样在大地上站住了脚跟。
“塔里木”在古突厥语意为“注入湖泊、沙漠的河水支流”。而“塔里木河”是维吾尔语,有“无缰之马”、“田地、种田”的双重含义。双重含义中的“田地、种田”,南疆是维吾尔民族的世居之地,作为世代与耕种为主业的农耕民族,他们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田地有着深刻的眷恋,于是赋予了“塔里木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淳朴思想。塔里木河蜿蜒流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在它流经的中游形成了南北宽达上百公里的冲积平原。这里河道曲折,汊流众多,沿河芦苇水草丛生,浩浩荡荡,“水上迷宫”,犹如“无缰之马”因而得名。塔里木河是保障塔里木盆地自然生态和各族人民生活的生命之河,她自西向东,所过之处,两岸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胡杨和沙漠植物,这些站立起来的河流,沿着塔里木河这条遒劲的血管,在沙漠腹地排列成了一道天然的绿色长廊,营造了大自然生灵共居的 。
是胡杨收留和养育了他们,那些西征的蒙古部落,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属。13世纪,蒙古人通过四个汗国征服了大半个世界,其中金帐汗国存在时间最长,统治俄罗斯达三百余年之久。18世纪,俄罗斯复兴了,桀骜不驯的蒙古土尔扈特骑士们开始怀念东方的故土。他们携家带口,整整16万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这些兴高采烈的游子们怎么也没想到“回乡的路是那么的漫长”,哥萨克骑兵追杀的马刀,从天而降的瘟疫与浩翰无边的荒漠沙海,一路走来,步步艰辛,饱经磨难,当他们踏进新疆,只剩了6万人。举目无亲的土尔扈特人一路行走,一路掩埋族人的尸体。他们含泪接受了中国皇帝的赐封,然后,搬进了莽莽的胡杨林海……胡杨林就像心胸辽阔的母亲为他们撑起了生命的大伞。他们在胡杨林中休养生息,繁衍子孙。两百年后,他们在胡杨林中恢复了自尊,与美丽的胡杨融为一体。
初夏的塔里木盆地,气温明显高于新疆其他地区。行走在塔里木河岸边的沙地上,松软的河沙柔软舒适。此时此刻,河水滚滚东流,沿途的胡杨林站成一排排忠诚的卫士,宁静而安详。水湾处,芦苇涌起微波绿浪,三两只野鸭煽动着翅膀在苇丛中嬉戏,时不时发出欢愉的叫声。正午是拱形的屋顶,太阳离地面最远,也最近。我们躺在被晒得暖洋洋的河床细沙上享受日光浴。此时的河流有些累了,只有大地的回声与我的心脏一起跳动,那些鸟儿似乎也隐入林中,变成了一个个树突,静止不动。
有些风物是 的,比如胡杨,它们需求的不是肥沃的土壤,而是足够的空间,辽阔的塔里木盆地满足了这个需求。在这些地方行走,时间总会带给人与众不同的厚重感。群鸟拍打着翅膀颂唱歌谣。一片稀疏的空地上,牛羊在悠闲地寻觅稀疏的草叶。一辆马车满载胡杨枯枝独行在河堤上,赶车人花白的胡须被风吹拂飘逸。在他的旁边,一位巴郎风华正茂,嘴里喊着一首令人费解的诗,不,是歌。赶车人偶尔扬起的鞭子只是象征地在那匹精瘦而强健的马背上拂过,其实无需这样的一鞭,老马也会知道回家的路,这只是赶车人的习惯动作,要不这样,赶车人会感到空旷和寂寞。不远处的炊烟扶摇而上,*昏是连接家与野外的润滑剂,走散的人,会随着一缕炊烟找到自己的家,或者一个缘分注定的落脚之处。此刻,在热瓦甫琴声的伴奏下,村庄进入了一天中最令人欢欣的时刻,歌声和琴声掀起了人们胸腔的情绪,欢快的麦西来甫有一种苍凉和悠远……
塔里木河的秋天,离天空最远,离大地最近,深沉的静美,就连奔腾的塔里木河,也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平静、舒缓、深邃而内涵。这是大自然值得欢庆的节日。微风吹来,金*的枯叶在天空纷纷飘舞着,恰到好处地撒在地上,很快就与沙土融为一体,随风而动的碎金,光芒耀眼。这时候,大地与天空,共同架构了无穷大的金色大殿。高不可及的穹顶下,牧羊人漫不经心地驱赶着一群羊,羊群踩着浮土和枯枝*叶,欢跳、嬉戏、咩咩叫着,细腻与粗矿,是大地上一枚一枚静止或者移动的斑纹,共同组成了大地、天空、树林和谐的自然图画。
而沙漠深处植物特性的张扬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领域或者层次之上。在库尔勒至若羌的千里长途,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鸡犬不闻,风是过客,沙是过客,水流是过客,偶尔的闯入者是过客,只有眼前的这些根,至死不渝地坚守着一个自然界的古战场缩影,饱经风霜的灵*在吟唱。被风沙剥去了*装的战士,铁骨铮铮,至死不降,胡杨的根、红柳的根、梭梭的根……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的根,空阔与孤寂中,一个宏大的抗击风沙的疆场,嘶鸣和灵*的呐喊破空而来。
历史就是那么奇怪,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听到的节奏,就像一架钟摆的声音,胡杨的根是时针,枝干是分针,风是秒针,它们的重叠,是胡杨林关于根的博物馆。抚摸根,就如同在抚摸久违的亲人,瞬间就让人回到了自己的原处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