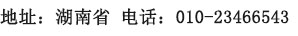岁被父母送人,在养父母家长大,又因为生病须终身服药。职校毕业,做过裁缝,开过百货店,26岁从苏中平原的家乡嫁到浙江,遭遇婚变,40岁离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在异乡生活17年,菜场摆摊15年,散漫地写作11年,已出版《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和《世间的小儿女》,后者登上了浙江省委宣传部推荐的“浙版好书榜”和《文学报》月度好书榜。陈慧没有想过会成为作家。
01
买她摊子上的砂锅夹、苍蝇纸、蚂蚁药、做衣服的顶针、打肉的锤子、割稻的镰刀、鱼刨子、暖瓶塞……等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的顾客,也不会想到,他们眼里的“阿三”竟然是个作家!菜市场里的摊主们、梁弄镇上的乡亲们都知道,摆摊的“阿三”风风火火,“像个男人一样”。
但是没人知道,她的文字,是非常温柔和清醒的。
“谁也不能触摸到我内心深处哪怕微小的一个喷嚏,然而,当这些我没有预想过的善意如同雪夜的火种那样辗转到我的手上时,我才明白自己一直就深陷在恋恋红尘中,从来没有拔出过自己的双脚。”
“你跟卖烧饼的说你上电视了,烧饼会便宜吗?出了两本书,日子没什么改变。我就是一个菜市场里的‘二道贩子’,写作是爱好,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普通人的生活浑身都是线头,一拉都散了。”“一个女人看似坚强,但原本应该是柔软的样子啊。”“如果能不当骑车的,而是去当坐车的该多幸福啊。”
“我安安静静地过,心里舒服。”“我只赚我能赚的钱,我选择宁静的生活。”“我不幸福,所以多做一些与幸福有关的事情,吃点好吃的东西,带孩子看个电影,回家和妈妈吵吵架。我不幸福,但我还和生活对付着,人的心是不满的,我看清生活后依然热爱她。”“生活才是最高贵的,我们可以编排文字,但生活是在编排我们。”“你有能力跟生活叫板吗?生活才是最高级的,你没有选择。我不是战士了,不去抗争了,它给了我什么我就顺着、贴着,让自己不那么难受。生活不会哄你,你只能认清它,融入它。”“灯泡像干瘪的橙子,而我则是贴地生长的牛筋草。”“过去的生活像是困在一口井中。其实我每次只翻动一块砖,我不停翻,就想透些光亮、让新鲜空气进来。”“那些年纪大的人,十多年了一直找我买东西,找不到我的话,会一直问我去哪了,那种感觉让我觉得人间是值得的,菜市场是值得的。”“生活不尽如人意,我愿意往回看。”
02
陈慧写道:
“很多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只是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样,端坐在我位于小溪边的山间房子里,慢吞吞地写着我想写的文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慧非常低调。
“可能是我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我也一直想让自己保持清醒。如果真成了网红,怕自己应付不了。所以我经常说,只要出现在菜市场,我还是那个小贩。这个定位是必须要认清的。”
在菜市场里,陈慧汲取写作的灵感。养父母“拉拉扯扯半生的婚姻”、铜匠遭大病后终于戒了烟、开杂货铺的老板娘说起疯儿子红了眼眶……这些都成为她笔下的人物。
“我写东西,不会死死扣住选题,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出的这两本书,所刻画的人物也都不是特地为了出书写的,它们更像是一种人物的集纳。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物有可写的地方,就会把他写下来。”“早上到了菜市场,我就全心全意去赚钱了,但不太忙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聊聊天。给我灵感的,也都是实实在在围绕在我周边的人,都是经历,也都是见闻。”
有时候,看到很有趣的人,或者很生动的场景,陈慧就会当场记下来。她有个习惯,就是会在推车里找出包装盒或是废纸,把这些细节先记录下来,形成一个梗概,再放在收钱的包里。等到创作时,再拿出这些素材做内容上的延伸。
0
至于为什么写作,她是这样说的。
写东西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结束了1年的婚姻,一场重病,让我终生服药。因为摆地摊卖百货很自由,刚开始我一边看孩子,一边卖货。孩子慢慢大了,我就静下心来写东西。
那几年,我是很难为情的。所以说,首先是苦难让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也给了自己一种新的活法。现在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个全民写作的年代,于我而言,出书也没什么。至于能顺利发行两本书,也是无心插柳的一个过程。所以“作家”这个身份,对我来讲,有点重。我觉得自己就是文学写作的一个爱好者。就像我早期的时候,我从没想过写下的东西有什么用,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写作”。关于什么时候再出书,这个都是随缘,看缘分。